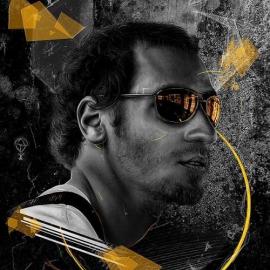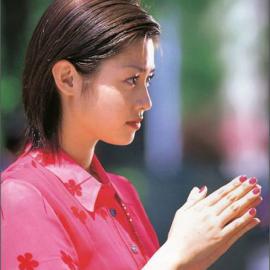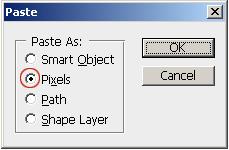何见平(柏林)和姜国良(广州)关于当下设计教育的对话
何见平给姜国良的信:
姜先生,您好!
冒昧平生,给你写信是看到您发表的文章――《谁能许65名学子一个未来?――对中央美院开设家居设计专业的质疑》。
我是生活在柏林的平面设计师。和您一样,我科班从浙江美院毕业,再来德国近十年了。但我对中国的设计教育一直留心有加(我的职业是柏林艺术大学的平面设计老师)。这种关心被我称为“学院情节”,正像您说的“她喜我亦喜,她忧我亦忧”。
我对中国设计教育的忧虑来自中国学院教育的大气候变化,十年前的所谓“精英教育”被改为“普及化教育”,这口号变化的背后,是大校园,大学科的心理。学院从什么时候开始,它不再是学术的领域了,被取代的是学生数,学科数,教授数的统计。但我们培养的学生――大学生的质量如何?每个学院心中有数,老师带的研究生留校,研究生带的学生再留校。
www.dolcn.com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到:
对待殊荣和奖项的心理与中国设计差距的存在也有内在的联结。太注重形式和单一以数据统计来看设计发展的方式会把设计带入误区,容易令自我膨胀。中国超过700家高等院校每年至少为社会提供上万名设计师或者说准设计师。按这样的比例是当之无愧的设计大国,但质量如何?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院校设计教育当负首责。设计教育应该有系统的学科建立,这个学科首先应该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
设计就是科学。它除了海报、CI还有太多的内容,被忽视的往往是设计史、艺术史等理论和哲学、文学、心理学等旁类学科。忽视理论加上大多数高校近亲式的教师培养工作,造就大量专业狭隘不合格的教师队伍。我不认为年轻一代本身有什么问题。
现代价值观念的改变本已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每年超过1000美金的学费培养的大学生如果在四年级还从未接触过字体设计课;不知道Helvetica还是一个设计师;能自诩为垮掉的一代却不知金斯堡为何人......难道不是这种教育质量出了问题吗?
设计是件平常的事,对设计师而言首先是件工作。设计也不应该是个心理膨胀的事业。它是文明社会的标志,但对社会进步更重要的还是化学、物理、数学和生物等专业吧!所以说到“使命”好象离设计远了。但每件工作自有它的意义。
这是我回答一位平面设计杂志编辑采访的片段,但我还是感到其中我们相同的话题。我今天冒昧来信,是我通过您的文章(虽然我对室内和建筑不是很专业),我肯定一点:在中国永远有清醒的人,只是我们的大气候把许多本该有机会引导别人的人的眼睛遮住了。
向您致意
何见平上
Jianping He
Hesign Studio Berlin
Duesseldorferstr. 48
D-10707 Berlin
Germany
姜国良给何见平的信:
何见平先生:
您好!收到您发自歌德和席勒的故乡的来信,非常高兴。您远在柏林,依然对祖国的设计教育“留心有加”,我应该对您表示由衷的敬意才是。我想,无论是您的“学院情节”,还是我的“校园愁”,都表达了我们对早年求学时的情景的怀恋――虽然宿舍是拥挤不堪的,图书馆和澡堂的位置也很有限,当然,更没有今天在校园周围的什么酒吧可“泡”,但是,我们依然感觉很幸福――今天回想起来,也还是那句话:青春无悔!因为,只因为当年在导师的教诲下,对自己学习的专业,对“设计史、艺术史等理论和哲学、文学、心理学等旁类学科”的几近“疯狂”的渴求。
由此,反观当下我国的设计艺术教育,真的弄不懂是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还是今天的年轻学子出了问题。对此问题,我之所以糊涂,是因为我也经常有象您一样的想法――“我不认为年轻一代本身有什么问题”;那么,若说教育出了问题,也应该说不通,因为今天在高校任教的教授,都应该和你我一样,有相似的接受教育的经历――对中央美院开设家居设计专业一事,美院内部应该有教师象我们一样提醒一下:“这样不妥吧”才是啊!当理性面临如此“悖论”,我很痛苦,请您代我就近到柏林大学请教请教当年的黑格尔教授吧。
另,对于您的"我对中国设计的教育的忧虑来自中国学院教育的大气候变化,十年前的所谓精英教育被改为普及化教育,在这口号变化的背后,是大校园,大学科的心理”一说,因题目大且复杂,容我下封信和您讨论。
还有,我准备把我们私人的通信,作为我的《谁能许65名学子一个未来?――对中央美院开设家居设计专业的质疑》一稿的延伸,以提醒他们慎重些,因为教育是事关未来的事情,对此,要有“赤字之心”。不知,您以为如何?
下次来信,请介绍些德国这方面教育的情况。
此致
姜国良敬上
2005年4月6日凌晨3点58分于广州